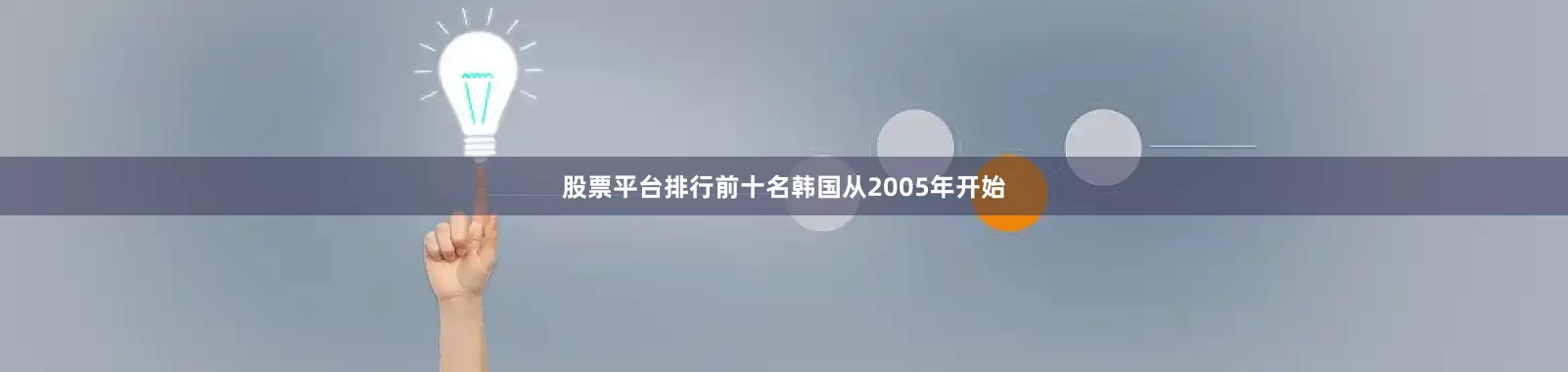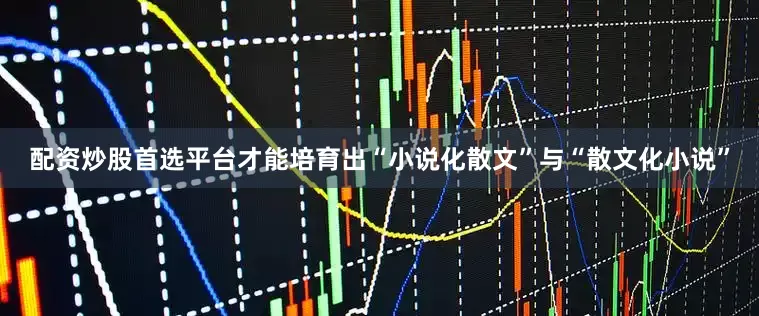
文化人类学家很早就揭示出,“分类”的本质缘于人类从混乱中建构秩序的需要。自古至今,出于建构文学秩序的需要,文学史学家们前赴后继孜孜以求于文类的划分,诸如有韵无韵的诗文之分及文笔之辩;再到近代小说、散文、戏剧、诗歌的文类“四分法”,总想在以简驭繁中,试图在文类间划出一道道鸿沟深深、边界清晰的红线。
散文与小说的分类,“本来只是借以描述文学现象的一种基本假设;在实际操作中,论者为了渲染其合理性,往往将分类标准凝固化。……倾向于强调‘边界’的神圣,并谴责各种‘越界’行为。(陈平原,《中国散文小史》,北京大学出版社,2019.)“名可名,非常名”,这种“类别划分已经取消了事物的独特本质。”(余秋雨,《北大授课》,北京联合出版公司,2020.)
展开剩余90%原本出于建构文学秩序需要的文类划分,延申到当代文学界,甚至还出现了一种潜隐已久的文类歧视现象:似乎没有文学创作天赋者才去搞评论;写不成小说者才退而求其次写散文;是小说家把写作剩下的“边角废料”施舍给了散文。仿佛在庙堂之高的小说面前,文学评论家气短,散文家个头低矮。同时,这种家族式的文体歧视现象,也造成了我们对艺术家碎片化、片面化的浅薄解读,乃至在某种程度上破坏了整个文学艺术生态的平衡。
就如,当我们习惯性地把作家墨白归类为“当代先锋小说家”时,其实也是对墨白整体文艺创作景观的最大遮蔽。面对近年来,墨白推出的两本散文集《鸟与梦飞行》(河南文艺出版社,2016.)和《通往青藏高原的道路》(河南文艺出版社,2024.),评论家们在潜意识中往往偏执地认为,这只是小说家墨白偶然小试牛刀的“客串”。墨白散文也常被评论家们有意无意地“忽略”,降格为墨白小说研究之余的“剩余物”,这也造成目前墨白文本研究的一个“盲区”,成为墨白研究的一个梗阻。
实际上,对于有强烈文学经典意识、常年坚持鲸吞式阅读、不断在大地上行走、文化素养全备、文艺创作全面的墨白而言,其文本库存中的诗歌、散文、剧本、绘画的量级同样不可小觑。我们只有与存量很大的小说作品等量齐观,才会在墨白研究中拥有辽阔无垠的研究视野,才能在墨白文本景观的整体观照中,看到云出岫中、霞蔚蒸腾的大气象,才能看到一个浑沦完整的艺术家形象。
道存万物,理一以贯,“大制不割”。文化无墙,文学无界,云层上面都是阳光。目前,散文创作中,上佳之作往往出自画家、科学家、考古学家、小说家、诗人们偶然为之的“客串”。鲁迅、沈从文、汪曾祺、孙犁、萧红、茹志娟等诸多前辈作家的成功探索,已经培育出了诸多文质兼美的文学“杂种”,这还包括现在正在走红的散文作家李娟、冯杰、塞壬、格致等,其散文书写也因为“越界”而别开生面,因为跨界而耳目一新。这种偶然闯入散文田野的跨界写作,打破了惯常散文写作画地为牢、纯而又纯的狭小格局,在有容乃大的驳杂中,扩展了散文书写的领地,扩大了散文书写的容量,丰富了散文书写的式样,呈现一种“杂花生树、群莺乱飞”的阔大气象。
作为归属“无韵”谱系的散文与小说,原本就同根同源,有着天然的血脉相通性与基因关联性,可谓你中有我,我中有你,“一脉之颤,十方震动”,“铜山西崩,洛钟东应”。“小说”一词最早出就现于中国散文之祖《庄子》一书。所谓质地纯净的散文与小说,所谓如井田制般畦垄整齐、界限分明的散文与小说,原本就是一个伪概念。当前散文书写中争论不休的“大散文”与“小散文”内涵的界定,写实与虚构关系的辨析,抒情、叙事、议论的比重等问题,也是一个伪命题。因为“散文是内心的直接外化,一个人的内心很可能有梦幻、冥想、寓言、童话的成分,因此也就了虚构。请读中国散文之祖《庄子》”。(余秋雨,《北大授课》,北京联合出版公司,2020.)小说就是广义的散文,散文与小说彼此互相借势生力,不断“团炼调和”杂交的散文和小说,才能品种改良,基因突变,促使种进种强。淡化文类,在散文与小说的模糊地带,才能培育出“小说化散文”与“散文化小说”,板结的土壤才会生长出一丛丛驳杂葱茂的文学景观。
敞开,是墨白散文、小说书写中共有的主题词。在墨白看来,散文、小说写作,说到底是一种文化观念与态度问题。现实主义书写是站在已知、全知的角度,一种有头有尾自我封闭的讲“故事”模式,而现代叙事是一种“对生命进程中未知探索”的“悬念”模式。(墨白《鸟与梦飞行:小说叙事的差异》)。法国思想家福柯(Michel Foucault,1926-1984)将现代性理解为一种态度,一种思想和感觉的方式,一种行为和举止的方式。伟大作家的“眼光”,正是对世界和存在复杂性、暧昧性、不确定性的深刻洞悉与尊重。
“不确定性”是指一种本质上的相对性。当代写作中经验和修辞的衰减,与我们自以为是乃至一知半解的日常文化态度密切相关。有人自作聪明地调侃:生活大于叙事,把想明白的交给散文,把想不明白的交给小说。其实,天下哪有彻彻底底想明白的事儿?恰恰这种“明白观”降低了写作的难度,玷污了写作的品质。环视当下那些自以为真理在握而见识浅陋、平庸乏味、泛滥成灾的所谓散文和小说,就会明白“绝对真理”往往是文学写作首先要面对的大敌。只有从平庸的文化现实生活中超脱出来,超拔才能使我们面对真正的伟大,才能让文学书写在呈现更多悬念般的未知中,永葆文学持久不衰的思想魅力。
在墨白的散文与小说中,我们都可以听到浓郁的精神寻根的“互文性回声”。以向远方“行走”为主题的散文书写与以人物离家“出走”为主题的小说书写,永远向深不可测的未知敞开,永远处于精神探险的进程中。如果说,向远方“行走”是墨白为自己散文书写设定的生命姿态。那么,离家“出走”就是墨白对小说人物生命探寻的尊重,是对纷繁复杂生命镜像的呈现:是“在我们庸俗不堪的日常生活中,承受着难以忍受的精神折磨”;是“因欲望而产生的恐惧、焦虑与抑郁”;是灵魂游荡、无家可归的苦闷与焦灼。“出走”的小说与“行走”的散文,在无限敞开中,互为表里,彼此呼应,呈现出文本杂糅的兼容与张力。
驳杂是世界的真相,也是生活的真相。任何真正的文学书写,都具有一种百川归海、杂取百家、兼容并包的杂质性与多维性。墨白《通往青藏高原的道路》一书,可作文化散文、生态散文、游记散文、文论随笔读之。用“小说家散文”为墨白散文命名,也是一种对墨白散文品质与容量削足适履的概念化界定。这里,我们不妨姑且笼统地称之为“墨白散文”。固然,“墨白散文”蕴含超出常规散文概念定义之外的诸多小说品质。墨白以小说家“旁观者清”的视角观照散文、书写散文。从《鸟与梦飞行》《我的大哥孙方友》《回忆某段时光》《生日快乐》《君子之交》《南丁先生》《民间美食》《铜山湖记》等诸多生活写实散文中,我们就可看出墨白作为小说家的写实功力:心细如发的细节捕捉,稍加皴染的场景描绘,敏感锐利的生活感悟,一寸一寸都是活的,就如威廉·莎士比亚所言的“所有人的生活里都有一部历史”。略举一例,墨白在《我的大哥孙方友》一文中,写其兄长、当代著名作家孙方友先生处女作发表的场景,小说笔法,微波粼粼,质朴无华,生动传神,可作“散文化小说”读之。
1978年的秋季,有一天上午,我们正在地里出红薯,堂姐又给大哥带过来一个大信封。大哥接过信封用舌头湿了一下他干裂的嘴唇,用他那涂满黑色红薯津的手慢慢地撕开那个信封。信封里出现了两本杂志,我看到大哥拿书的手都在颤抖,那是两本一模一样的杂志。他轻轻地翻开其中的一本,突然一下子跳了起来,顺着红薯地朝河道奔跑起来,他一边奔跑一边叫着:发了——我的小说发了——
起初,我们都被大哥突然出现的动作吓着了,等我们明白过来,也朝河道追过去。等我们追过去的时候,大哥的情绪已经平静下来,但是有泪水从他的眼睛里流了下来。他对我说:发了,你看,真的发了——我的小说发了——
在这个日益同质化的时代,很多作家感觉迟钝,情感麻木,“写实”无力。评论家王干先生发现当下很多作品中“景物描写”缺失,原因就在于,在钙质化的坚硬传统“景语”遮蔽下,在当前“共情”的语境下,我们已经被长期约定俗成、习焉不察、共生共用的“景语”套牢,诸如“露珠晶莹”、“阳光明媚”、“杨柳风轻”、“雨恨云愁”、“月华如练”、“晓风残月”、……拘囿于这些拾人牙慧油滑顺溜的“景语”中,“风景旧曾谙”,我们无景可写,无景能写,无景会写。“写实”无力还表现在,情感衰退、真情流失、伪情泛滥、“情语”无味的所谓“零度写作”中,冰渣横流,贫血苍白;还表现在人物书写中的失真变形、呆板无神、单薄虚浮中。写景叙事、状物写人的贫弱,是当下写作中的通病。
墨白小说、散文,边界模糊,互为渗透,多棱角呈现,其精熟的写实功力,提升了其“小说化散文”的精神品质。在“通往青藏高原的道路”上,墨白以扎实的笔力,把邂逅的一个个人物,一一定格在瓷实饱满的文字里。比如,对那位“陌生的兰措”的“一切景语皆情语”的白描:
在阳光下,我注意到了兰措那因被强烈的河风过度侵蚀的皮肤和干裂的手背,也注意到了她那因被强烈的紫外线揉搓而变得粗糙的面颊。兰措用一只水桶从水井里提水,再倒入身后的水桶里。她在我们这些陌生人的注目下,似乎有些仓促地挑起两只橘黄色的水桶,沿着来时的小路匆匆往草黄色山坡上的家走去。
审视当下大量泡沫式散文泛滥而无效的书写,其实还是自身有意识地降低了散文书写的门槛儿,减低了写作应有的难度。要知道,只有有叙事难度的作品,才经得起智力的挤压,就如王蒙评论《红楼梦》所言,“经拉又经拽,经洗又经晒”。任何没有超越性、“硬核”缺失的平滑散文写作,都是流水账式的“记录”,都是涎水流淌式的分泌物。固然决定文学书写质量的因素很多,但是起决定性作用的是人生体验的深度。泡沫式书写缘于作者生活体验范围的狭窄和认知的浅薄,在人云亦云中无限繁殖,在写作官能症的神经质中无节制地涂抹。
古人说:“天道无隔,一通百通。”这里的“道”,就写作而言,就是“文道”、“人道”、“世道”。当今,“无道”写作的根源就在于,很多人把写作冲动当才气,把所谓的才情当成取之不尽的能源,把有限的阅历当用之不竭的写作资源。“道”是写作的“硬核”,而有“通道”“通识”硬核的写作,才是真正的写作。一以贯之墨白作品的“硬核”,是“行进在探寻未知过程中”的文化考察,是悲悯之气遍布小说的人生追问,是“用自己的话语权力建造圣洁的领地和人生的境界”的执著坚守。墨白读书随笔、创作札记中有大块儿的思想颗粒与精神结晶体。从《面对死亡》《网络时代,我们怎样做“上帝”》《做一个气质高贵的人》《生活从来就不是容易的事》《语言的权力》等篇目中,可看出墨白的阅读观,“阅读就是在寻找自己的无知,是一种有重量的精神运动”;可看出墨白要成为“精神贵族”的人生观;可看出墨白散文书写中思想的深度与精神的亮度。“道”的钙质,在墨白小说中聚变成无数光粒,在“裸奔的时代”,照亮“别人的房子”,透射出物质化时代无尽的“欲望与恐惧”。
如果说,“道”是散文与小说的“硬核”,那么文化就是散文和小说最坚实有力的基座。最高的写作呈现的是文化的底色,套用席勒的话“国家太小了,世界才是我们的题目”,对于有世界文学眼光的墨白而言,文学太小了,文化才是我的题目。当下,诸多散文、小说书写,最大的败笔表现在文化上。文化视野狭窄,文化认知粗陋,文化底蕴浅薄,文化精神困窘,一身文化“贫相”。文化常识匮乏,累累文化硬伤,经不起文化推敲。阅读《通往青藏高原的道路》一书,我们能感觉到年逾古稀的墨白有着异乎寻常的文化饥渴感,有着时不我待的文化探险欲,有着打通散文、小说文体相隔的急切感,在更大的文化视野中,在“处处隐藏着鲜为人知事物”的青藏高原边缘地带,“全面地认知我们所生存的世界,认知生命的本体,并以此来校正我们前进的方向”,因为这是“一个只有抵达青藏高原之后才能抵达的世界”。
文化兜底的散文书写,其探路行走、觅食找水般的文化探寻,是墨白为叙事赋值增能的生命践履。在“迁徙的村庄”中,探寻“那些隐藏在人类内心的秘密”;在“旅欧散记”中,发现永恒的自由“永远存在于我们的想象里,永远存在于我们的生活里”。再“通向青藏高原的道路”上,不是常见的“到此一游”后,匆忙兑水稀释而成的导游词,而是水乳交融同呼吸共命运般的生存体验,是潜入文化深处的打捞,是叙事理念的浴火重生。“以青藏高原为背景对人生与社会的感悟”为思考的着力点,“在拥有了丰富的人生经历和切肤的生活感受之后,怎样才能成为小说家”;在“东巴纸”制作、纳西音乐中“寻找小说的灵魂”;在东巴文的雕刻中思考“结构故事的能力”,在冰川雪山中,感悟“艺术的真实性”;在“天果洛、地果洛”中,体悟人类生存的内涵;在考察《格萨尔》的传播中,发现藏地“史诗”书写的文化路径;在经筒的转动中,思索文学与音乐的关系;在“三江源的野生动物”群落中,“想通过一颗野草来感受生命的过程,通过一只飞鸟来感受精神的飞翔”。在文化探寻的无限铺展中,墨白的写作触角伸展到了文化的缝隙中,小说与散文,生命与世界,“花非花,雾非雾”,混沌一片,苍茫无限。
■原载《郑州师范教育》2025年第3期
发布于:河南省我要配资平台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